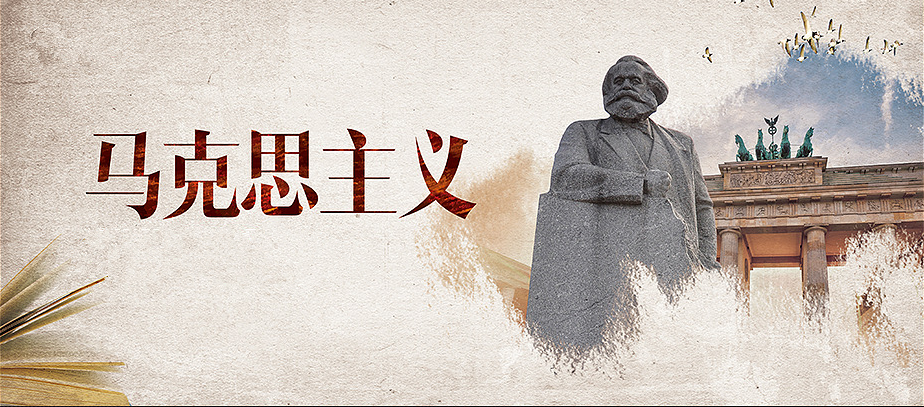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新境界
姜翔
摘要:文章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的学习,进一步厘清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质。从唯物史观、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从“生态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现实方案”三方面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创新。
关键词: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马克思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新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8-0240-0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丰富且深刻,核心就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主要内涵是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①,主张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进而建立互商互谅的友好伙伴关系。在安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厘清了“中国威胁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权,中国坚持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零和博弈思维”②,以合作共赢的思维方式,达到双赢、多赢、共赢的结果。文化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文明冲突论”,而是奔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达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美好愿景。在生态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文明共识,“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道。它体现了一种高举远慕的心态;呈现了慎思明辨的理性;传递着一种体会真切的情感;暗涌着执著专注的意志;奔向于一种洒脱通达的境界。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
唯物史观是共同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形态主要划分为“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两个历史阶段,它们分别对应着“物的依赖性”状态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状态。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每个人的发展都依赖于社会的不断前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1]。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共产主义作了深刻揭示,共产主义是对分工、异化和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③,它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获得“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实现“自主活动”的自为性、自发性、自在性。由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继承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并发展了新时代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它不是人们的经验常识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它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象,来看待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与世界的图景。从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困境出发来探究改造世界的有效方案,并把世界人民看成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
共同体是共同的实践形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到:“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他首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人只有作为历史的经常结果,他才成为历史的经常前提。”马克思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是一种历史的实践的存在,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2]实践关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历史关系。”因此,“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个人与共同体辩证统一的社会。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把共同体作为自己的实践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思考“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后,通过调整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达到人类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双重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同马克思的共同体都是在共同体的实践形式下,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同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目标。在现代化的转型期,人的矛盾性不断显现出来,精神的贫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与自然的疏离,这些都表现出人类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的三种属性间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探寻人类崇尚的自由。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主体性为原则,构建一个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提高、个人素质不断完善的社会,进而给人们营造一种由外在的被动转化为内在的主动型的生活状态。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宽了马克思共同体的研究领域,突破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空间发展,并不断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注入新血液。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是重要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描述的“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前提和基础”[4]比较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经济领域拓宽到了生态领域。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间的矛盾的现实,在生态领域更是倡导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这从理论与实践上使“生态命运共同体”理论深深嵌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拓新。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重要的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强调了以劳动为基本的利益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利益的理解是从“现实世界”跨越到了“虚拟世界”,以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为基本点,拓展到了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新的拓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方案。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的理想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他表述了三种社会形态并提出了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路径,但社会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探讨并提出高度抽象的共同体形态,旨在揭示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运动规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在人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下,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想预测由抽象变为具体,由理想变为现实,使其既有理想的目标,也有现实的途径;既有蓝图规划,也有可操作性、可行性的方案。相比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的超验性和彼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加强调经验性和此岸性。目的在于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不断促进世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注释:
①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②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③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责任编辑:杨国栋








